生命的交相辉映与生活的内置互换
——读张明辉诗集《身外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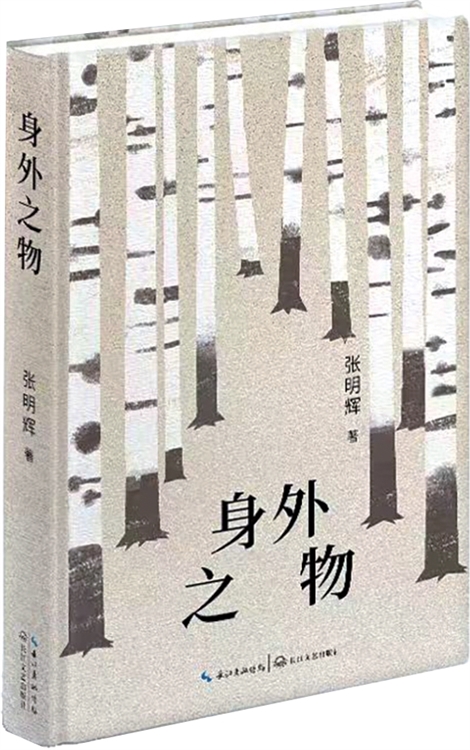 |
郭园/文
诗人张明辉在《身外之物》的自序中谈道,当他沉浸于山水之中,内心便安静下来,触觉变得十分灵敏。在那一刻,他穿行于天地自然的丛林之中,走近那些山水河流、花草树木、鸟兽鱼虫,感知着身旁的雨露晨光、晦明变化,仿佛实现了与自然的对话,达成了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共同的呼吸开合、节奏律动。置身于更广大微妙的生命圈层、生命场域中,人们在经历过身心的洗礼后,与山水相呼应,与草木同呼吸,便能体察到生活的平凡与可贵、生命的渺小和高远。“人是自然之子,也是灵性之子”,是山水滋养了诗人的灵魂,滋养了他的诗歌和文字。
人类世界的生活从广袤的自然生活中分离出来,而诗人又转头回到自然的怀抱,拥抱着生活的朴实和平凡,寻觅着生活的静美和灿烂,这是他对人世生活的热爱与赤忱,对广大世界、万千生命的完全敞开和释放。“在喧嚣的尘世,人是孤独的。当你真正进入自然的山水,在青草间呼吸,便会产生愉悦、舒展和自由。”可以说,张明辉的诗歌源于山水草木和那些奔跑跳跃于自然世界里的鲜活生命。
“我并不惧怕黑夜/却在黎明出门时担心/被雨淋湿/被这个混沌的世界吞没/我是如此之小/却又如此卑微”(《如此之小》)。生命纤细如发丝,更坚挺如巨石,当现实生活和世界的浪涛狂奔袭来时,如何持守本心,保持自我的独立和清醒,这是诗人着重思考的问题。人类之于宇宙,渺小得仿若一粒尘埃,一滴水、一口空气都能致他于死命,但人却比致他死命的东西伟大得多,因为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苇草。诗人说,蜷缩在被窝里与尘世隔绝,却仍要拉开窗帘与外界接壤,让风钻进来,感受着风的速度和温度,他并不惧怕黑夜,怕的是被混沌所吞没,对生命的虔诚、对世界的敬畏油然而生。从世界之大和自身之小中,诗人理性地观照着人类世界和社会,观照着山川大河、日升月落,抵达了生命的纯真与纯粹。
行走在现实生活的场域,穿行在山水自然的丛林,遨游于世界的广袤和生命的细微之间,当生命与生命隔空对望,便勾连起人们对往昔、当下的感悟和对未来的畅想。在生命的两相对照中,在“内我”与“外我”的碰撞弥合中,在时间、空间交织缠绕的复杂场域中,诗人通过对自然风物的吟咏,达成了“我”与外部世界、生命维度的自恰平衡。
不论是在水边、在山野还是在林间,都是诗人对岁月的感慨,对时光的遥望,对身心宁静的寻觅,对生命韵律和节奏的记录和观照。张明辉力求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去感知,书写下最真实、最感性、最明亮的生活过往,打捞起那些宛若碎钻的生命断面和横截面,摄取下自然美好的时光印象。正是那些此起彼伏的声音、那些花月云雨、那些无聊与精彩,构成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用一生去亲近泥土/亲近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时间的藤在不断抽打/苦涩从记忆中剥离了/存在即虚无/光阴也是虚无/人戴着面具行走”(《在水边》)。在时间中慢慢变老,在空间里慢慢变好,总能枝繁叶茂,那些酸甜苦辣、欢喜悲戚都沉淀在时间的流沙中。时间仿佛一位魔法师,带走人们的欢喜和忧伤,抚去人们心中的苦痛和创伤。
“他活在一首诗里”,写诗多年,诗歌已然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对生活的回望与凝眸中,张明辉以文字的分行为介质,安放着自我精神的丰盈和空虚,浸透着灵魂的润泽与饱满,贯通着情感的流动和回环。诗人从过往的时刻中挖掘着平凡与惊险,感受着海风的游荡、芦苇倒伏的凄美,怀念着海边的生活,这是少年时刻的回忆与珍藏,这是海洋时刻的绝美和畅想。在《怀念海》这首诗歌中,那时候的“我”用孤灯去放牧海,在潮水激荡中豁开礁石的壁垒;用目光去触碰海,潮水奔涌之间,卷起飞翔的欲望……“孤灯”“目光”与海洋交织,碰撞出诗人与亲人们的独家记忆,不论是四处游荡着的咸湿海风,亦或是渔网捕捞上岸的往事,它们都成为萦绕在诗人脑海耳畔的故土交响、生命吟唱、祖辈见证。用思念撞破礁石的壁垒,以激荡的潮水卷起生命的期待和向往,由此抵达了一种倒伏和站立之间的凄美与哀伤。当诗人用文字将这些思念的情感、怀念的情思记录下来时,眼前便浮现出茂盛蓬勃的记忆重叠与灵魂新生。
张明辉说:“诗歌应从人性出发,从情感出发,自我流露,直抒胸臆。诗歌乃自然生发,应怀赤子之心,不故弄玄虚,不沾染功利,故诗集命名为《身外之物》。”在时间和空间的长河中,将自身融于天地,融于自然,不以诗歌谋功利,不以诗歌乱呻吟,不以诗歌相攀附,让诗歌回归诗歌本体,这是诗人张明辉的诗歌美学追求和精神投影。在他走进自然的那一刻,在他将自己交还给山水林田湖草沙的那一刻,他达成了生命与生命间的交相辉映,完成了个人灵魂与生活内置性的契合互换。
